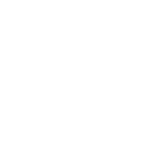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婆婆来了剧情介绍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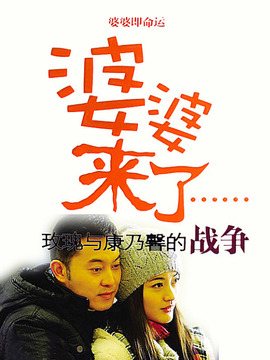
01
结婚当天怪异的习俗
她来自江汉平原,博士。2013年嫁到林家,丈夫是闽南人。结婚当天,身上的大红衣服、媒婆撑在头顶的大红伞、门槛上待跨越的火盆,让她颇不习惯。更意外的是,因为生肖冲突,作为至亲的小弟和三叔,在新娘入门那一刻必须回避。据说,这一刻新娘身上有强大的煞气,生肖冲突者如果不回避可能有生命危险。天啊,还有比福建人(闽南人)更迷信的吗?
女博士在大学研究社会学,后来发现结婚当天种种怪异的做法和说法,很难简单归结为迷信,这体现婆婆来了剧情介绍了她从一个外人转化为自己人的过程。对一个家族来说,血缘网络牢牢限定了自己人的边界,一个外姓女人的融入,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是的,生活总是比理论更加复杂。

02
生儿子的偏好
结婚前,姐妹朋友们提醒她,嫁哪里都可以,坚决要避开福建(尤其是闽南)和广东(尤其是潮汕)!闽南和潮汕地理接壤,文化如出一辙,特别是生儿子的偏好。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尤其是从女性地位奇高的江汉平原出来的她,当然不愿接受“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传统。在反复和未来的丈夫确认婆婆来了剧情介绍他们的婚姻将不以生儿子为终极目标之后,她才同意结婚。虽然丈夫多次表现出“生男生女都一样”,甚至“生女儿更好”的态度,但她依然心存忐忑,她知道症结不在丈夫身上,而在婆婆那边。婆婆没有明确要求她一定要生男孩,但每次看到婆婆提起谁谁家又生了一个男孩时表露出来的艳羡神情,她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的一个学姐,也嫁给福建人,因为生的是女儿,公婆非常沮丧;公婆的另外一个儿子在此之前已接连生了几个女儿,他们都把生孙子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没曾想事与愿违。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学姐的公婆知道,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明里暗里建议她老公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确保第二胎是个儿子。为这事,两口子真没少烦恼。学姐知道,没有男孙来传承血脉的话,她的公婆永远会觉得人生的任务没有完成,他们在村落社会中也将丧失尊严。
最近,学姐的婆婆以各种不适应为理由,不愿意继续在雾霾沉重的大城市为他们带孩子。实际上她很清楚,如果她生的是个男孩,婆婆再不适应,也会留在城市为他们带孩子的。
03
神灵秩序的解释无懈可击
除了血脉沿承的信仰,闽南人将大量的精力都投注在拜神上面,她老家的人很少这么做。每年春节回家,婆婆都要按照神仙生辰准备各式供品,神仙们散居于屋子内外的各个位置,拜的时候,除了要看准时间,还要看准地点。除了家里的神,还有庙里的神仙,都需要恭恭敬敬祭拜。祭拜的几乎都是妇女,婆婆每次祭拜的时候总是带着她,显然是希望她能逐渐习得这一技能。问题是,神仙多、规矩多,跟了几个春节,她还是不能独立操作。
因为怀孕不久,她和丈夫商量着今年不回家,让婆婆来广州过年。丈夫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说服他妈妈?最大的难点是如何解决拜神的问题,春节不拜神,几乎不可思议!想了几个替代方案,他们给老妈打电话商议。听说要到广州过春节,婆婆第一句话就问,“那拜神怎么办”?他们提供第一个方案:在广州找个地方拜一下。被直接拒绝了,没有理由。第二个方案:提前把各路神仙都拜一遍,再来广州过年。也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个没有道理”。婆婆想了一下说,要不你们在广州过年,我在老家过年?她听了不免有些郁闷,婆婆为了拜神,宁愿和他们分开过年!这个方案被他们否决了。踌躇之际,婆婆想了一个奇妙的方法:让已经出嫁的妹妹代为拜神!还好,妹妹是嫁到附近的。
初三,正吃午饭,婆婆提出一个问题:老家正在建庙,我们家是捐四个人的钱,还是五个人的钱?这个问题估计她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老家修庙的事情去年已经说了,理事会提出,每人收500元。按照目前的人口,他们家只有四口人,除了他们两口子,婆婆,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婆婆的意思是,最好还是按五个人交钱,反正也就多五百块钱,图个大吉大利。为增强说服力,婆婆举了隔壁村的一个反面案例:隔壁村早些年修庙,有一户人家儿媳妇怀了孩子,为省钱只多交了半个人的钱,结果生出来的小孩智力有问题。神仙灵验得很,你们不要不信!
这个案例即使是真的,应该也是偶然发生的,不见得真的是神明报复。但是在婆婆的生活世界中,神灵秩序往往是解释各种偶然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别人都敬神而你不敬神,那么你遭遇意外事故自然是受到神遣;如果别人敬神你也敬神,意外事故还是落在你身上,那说明你不够敬神;如果你比别人还敬神,意外事故还是落在你身上,那说明你上辈子触犯了神明。总之,神灵秩序的解释几乎是无懈可击;你若信之,它会为你提供一套解释所有挫折与不幸的话语体系,让你即使经历各种苦痛,最终也总能心平气和地生活下去。
04
冲突的解决
血脉沿承的信仰,向下是生儿偏好,向上则是祖先崇拜。有祠堂的,大家就在祠堂祭拜祖先;没有祠堂的,则各自在堂屋里祭拜。与神灵崇拜一样,祖先崇拜也需要严格遵守时间,也要准备相应的供品。在她看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一起,共同塑造了闽南村民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形塑了他们日常的生活模式。他们的时间几乎是围绕各种祭拜活动展开的,祭拜之外,他们的生活总是显得悠闲自得,串门、喝茶、聊天,可以花掉大半天的时间。她猜想,他们的食谱和味觉都是由祭拜的供品体系塑造而成的?难道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吃不惯闽南菜的根本原因?
作为江汉平原的女性,她更习惯于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与丈夫家总是格格不入。几年来,她发现冲突其实挺难解决的。在她看来,冲突的解决,无外乎三种可能:要么丈夫足够强势,敢于背叛或局部改造生养自己的文化体系;或者自己足够弱势,愿意融入丈夫家庭所在的文化体系;还有就是双方的妥协,但是微观的妥协方案往往不牢靠。
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革(个人化?自由化?),毕竟我们不可能集体回到传统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宗族村庄的现代革命还远未完成,虽然所谓的现代生活也会带来别的烦恼。但是,从日常社会学的角度看,她也许更需要的是微观结构的改变(自己家庭的权力关系变革),而不是等待一场彻底的宏观结构革命来改造其家庭生活。这就是矛盾所在。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副研究员林辉煌。编辑:IPP传播。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拥有一支以郑永年教授为领军的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微信ID:IPP-REVIEW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